《景觀:文化�����,生態(tài)與感知》一書自1998年初版至今��,已過去七個(gè)春秋�����。這期間中國社會發(fā)生了巨大的變化,這種變化更體現(xiàn)在中國社會關(guān)于景觀和相關(guān)學(xué)科及職業(yè)的態(tài)度上���。本書的初版和再版內(nèi)容��,實(shí)際上都是與這些重要的社會發(fā)展和學(xué)科發(fā)展緊密相關(guān)的�����。所以���,我希望讀者能把本文集放在這樣的社會和學(xué)科發(fā)展背景中去閱讀。
第一大值得在此紀(jì)念的是中國社會��、特別是中央政府和國家主管部門的科學(xué)景觀意識明顯增強(qiáng)��。這可以被看作是2003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的科學(xué)發(fā)展觀的具體體現(xiàn)�����。記得作者曾在1998年發(fā)表了對缺乏生態(tài)和科學(xué)意識����、大地景觀意識的“小農(nóng)式園林”進(jìn)行批判(見本書“世界園林專業(yè)發(fā)展的三個(gè)階段看中國園林專業(yè)所面臨的挑戰(zhàn)和機(jī)遇”一文)��, 2000年又發(fā)表了對城市“美化運(yùn)動(dòng)”和形象工程的批評文章(“國際城市美化運(yùn)動(dòng)之于中國的教訓(xùn)(上)”����,“國際城市美化運(yùn)動(dòng)之于中國的教訓(xùn)(下)”���,中國園林,1:27-33��,2:32-35)��,當(dāng)時(shí)還有不少專業(yè)人士深感不解���,并用很激烈的方式打電話來表示抗議��;到了2002年5月����,國務(wù)院就發(fā)出了關(guān)于加強(qiáng)城鄉(xiāng)規(guī)劃監(jiān)督管理的通知(國發(fā)[2002]13號文件)�����,和隨后的九部委聯(lián)合發(fā)出的關(guān)于貫徹國務(wù)院通知精神的文件,明確批評了城市景觀建設(shè)中的錯(cuò)誤做法����。之后,2004年2月���,建設(shè)部���、發(fā)展和改革委員會、國土資源部和財(cái)政部四部委聯(lián)合發(fā)文��,明確提出暫停城市寬馬路�����、大廣場的建設(shè)��。2005年5月底由建設(shè)部組織在揚(yáng)州召開的有500多位市長���、城市規(guī)劃和建設(shè)主管部門領(lǐng)導(dǎo)參加的“城市水景觀和水環(huán)境治理國際研討會”����,則可以被看作是一次傳播生態(tài)和科學(xué)景觀理念的具體行動(dòng)�����。
第二大令人欣慰而值得紀(jì)念的事是,2004年12月����,“景觀設(shè)計(jì)師”被國家勞動(dòng)與社會保障部正式認(rèn)定為一個(gè)新職業(yè):一個(gè)以協(xié)調(diào)人地關(guān)系為終身目標(biāo)的崇高職業(yè)。這一新職業(yè)通過2005年5月6日的中央電視臺���,以一個(gè)13分鐘的���、完整的《焦點(diǎn)訪談》節(jié)目,向全國公布和介紹��,這在任何一個(gè)職業(yè)的發(fā)展史上無疑都是一種榮耀��。這又令我想起1997年底��,為了注冊北京土人景觀設(shè)計(jì)研究所��,工商管理部門甚至拒絕使用“景觀設(shè)計(jì)”一詞���,因?yàn)榇_實(shí)沒有這個(gè)行業(yè)。經(jīng)過艱苦的解說工作之后����,方勉強(qiáng)得以通過���。而如今再看舉國上下的“景觀設(shè)計(jì)”單位,已是林立街頭����。在令人激動(dòng)的同時(shí),卻又生許多愁苦:諾大中國����,長期的教育缺失,畢竟沒有多少合格的景觀設(shè)計(jì)師����。發(fā)展景觀設(shè)計(jì)教育已是迫在眉睫。
第三件值得所有關(guān)注中國人地關(guān)系命運(yùn)的人們歡呼的事是�����,中國的景觀設(shè)計(jì)學(xué)科發(fā)展及教育方面業(yè)已經(jīng)有了巨大進(jìn)步��。記得在本書初版前言中曾呼吁:中國急需一個(gè)學(xué)科來協(xié)調(diào)嚴(yán)峻的人地關(guān)系�����,這個(gè)學(xué)科就是景觀規(guī)劃設(shè)計(jì)。之所以如此呼吁��,并不斷放大而未曾停歇�����,是因?yàn)?����,?dāng)時(shí)與景觀設(shè)計(jì)相近的一個(gè)傳統(tǒng)學(xué)科:風(fēng)景園林����,剛剛因?yàn)橐粋€(gè)非常荒誕的理由而被取消���。這既是一個(gè)悲劇,同時(shí)����,又何嘗不是一個(gè)新學(xué)科誕生生的契機(jī)。它給原有舊專業(yè)一個(gè)脫胎換骨的機(jī)會��,走出封閉的小農(nóng)式園林�����,在其身后留下一堆完整的遺產(chǎn),任其雖處鬧市�����,而無聞車馬���;沉醉桃園��,而不知有秦漢��。而這個(gè)新生的胎兒則將破殼而出��,勇敢地承擔(dān)起拯救城市��、拯救生命土地的重任���,它的乳名是“景觀設(shè)計(jì)學(xué)”,大名“土地設(shè)計(jì)學(xué)�����。”在這一目標(biāo)指引下���,北京大學(xué)于2002年11月在原有景觀規(guī)劃設(shè)計(jì)研究中心基礎(chǔ)上�����,正式批準(zhǔn)成立景觀設(shè)計(jì)學(xué)研究院��,一個(gè)以招收研究生為主的二級學(xué)院���,并于2003年4月的非典期間召開成立大會����。來自全國的近800名熱心支持者齊聚燕園���,見證了這一盛會���。不到一年后,清華大學(xué)成立了景觀學(xué)系����,其它類似的專業(yè)和院系相繼在全國各大院校紛紛出現(xiàn)���。
國家建設(shè)部積極促進(jìn)景觀設(shè)計(jì)學(xué)科教育的發(fā)展�����,并于2004年12月成立了由北京大學(xué)���、清華大學(xué)�����、北京林業(yè)大學(xué)��、同濟(jì)大學(xué)等18所院校組成的全國高等院校景觀學(xué)(暫定名)專業(yè)指導(dǎo)籌備委員會(籌)�����,中國建筑工業(yè)出版在積極組織編寫系列教材����。
國家教委����、教育部和國務(wù)院學(xué)位委員也對景觀設(shè)計(jì)學(xué)科的發(fā)展給以高度重視。2005年6月�����,國務(wù)院學(xué)位委員會正式批準(zhǔn)在北京大學(xué)設(shè)立景觀設(shè)計(jì)學(xué)碩士學(xué)位。第一批20多名景觀碩士研究生將于2005年9月入學(xué)�����。與此同時(shí)���,風(fēng)景園林學(xué)科也“起死回生”���,并同時(shí)由國務(wù)院學(xué)位委員會批準(zhǔn)設(shè)立在職人員風(fēng)景園林專業(yè)碩士學(xué)位。北京大學(xué)�����、清華大學(xué)���、同濟(jì)大學(xué)��、北京林業(yè)大學(xué)等全國多所大學(xué)被作為試辦單位�����,2005年首批招生���。使風(fēng)景園林(景觀設(shè)計(jì))專業(yè)學(xué)位,如同工商管理碩士�����、工程碩士一樣���,成為一個(gè)專業(yè)學(xué)位��。在中國相關(guān)學(xué)科的發(fā)展史上���,不能不說是一件具有歷史意義的大事,與此前不久風(fēng)景園林學(xué)科被取消的事實(shí)相比����,無疑是一次翻天覆地。
第四件值得在此紀(jì)念的事是發(fā)生在2004年5月至7月的一場前所未有的大討論����,多位權(quán)威專家都卷入了這場可以稱為爭論的學(xué)術(shù)大辯論(見中國園林,2004年第5,7期)��。爭論的直接原因是作者和李迪華發(fā)表了一篇題為“《景觀設(shè)計(jì):專業(yè)學(xué)科與教育》導(dǎo)讀”(中國園林��,5:7-14),但更早的原因是收入本書的“世界園林專業(yè)發(fā)展的三個(gè)階段看中國園林專業(yè)所面臨的挑戰(zhàn)和機(jī)遇”一文�����。從學(xué)術(shù)的角度來看�����,這無疑是一場具有重要意義的爭論���。它有利于澄清關(guān)于Landscape Architecture的認(rèn)識����,并使人們更加清楚地認(rèn)識到傳統(tǒng)風(fēng)景園林學(xué)科的局限性和進(jìn)一步拓展的迫切性�����。本書新收入的“還土地和景觀以完整的意義:再論‘景觀設(shè)計(jì)學(xué)’”一文����,反應(yīng)了這場大辯論的一些核心內(nèi)容。景觀設(shè)計(jì)學(xué)與傳統(tǒng)園林學(xué)科的分野由此可以看得清清楚楚��。當(dāng)然��,社會上名稱的濫用掩蓋了一些實(shí)質(zhì)性的內(nèi)容。因此���,為了讓世人更清楚地了解景觀設(shè)計(jì)學(xué)科的內(nèi)涵�����,在學(xué)術(shù)的范圍內(nèi),我寧可稱Landscape Architecture為“土地設(shè)計(jì)學(xué)”��。景觀規(guī)劃設(shè)計(jì)師應(yīng)該認(rèn)大禹���,而非魯班和計(jì)成為祖師:“左準(zhǔn)繩����,右規(guī)矩���,載四時(shí)�����,以開九州����,陂九澤,度九山���。令益予眾庶稻����,可種卑濕��。”�����。本文集關(guān)于景觀文化���、生態(tài)與感知的研究���,正是建立這樣的一種認(rèn)識上的?��;仡欉@7年來學(xué)科發(fā)展上的風(fēng)風(fēng)雨雨和巨大的進(jìn)步����,再重溫周干峙院士在初版序言中的話語:“凡是真正的搞學(xué)術(shù)�����、做學(xué)問的人都是不怕有爭議的,”真可謂意味深長�����。
我特別感謝李迪華老師7年來始終如一的支持和幫助����,我仍然清晰地記得當(dāng)我離開載我回國的航班���,踏入北大校園的那一刻開始����,我便感受到了今后的學(xué)術(shù)道路必將不會孤獨(dú)����。共同的理想和社會責(zé)任感,使我們能風(fēng)雨同舟��,在重重的困難面前�����,互相勉勵(lì),并任勞任怨��,從不放棄�����。
除了初版中已經(jīng)感謝的老師和學(xué)生們以外���,我在這里還將感謝這7年來與我一道共同創(chuàng)業(yè)和參與研究的同事和學(xué)生們�����,他們包括(但不限于):潮洛蒙����,周年興����,韓西麗,劉海龍��,李偉�����,朱強(qiáng),白磊����,張蕾,李小凌��,黃剛���,姜斌��,裴丹����,鄧細(xì)春�����,王建武����,郭凌云���,李春波����,張志文,轟偉�����,楊崢嶸����,彭德勝,劉向軍��,張慧勇��,王浩���,徐剛����,陳彪��,呂晉磊�����,張紅,陳利靖�����,賴茜���,劉君等���。
我同時(shí)非常感謝這幾年來共同關(guān)心有關(guān)學(xué)科的發(fā)展并因?yàn)橛^點(diǎn)的相同或不同而在學(xué)術(shù)刊物上或其他場合對本人進(jìn)行的鼓勵(lì)、仰或批評和指導(dǎo)的前輩們���,他們包括(但不局限于)陳有民�����、陳自新��、程緒珂,崔海亭��、甘偉林�����、何濟(jì)欽、黃潤華��、李嘉樂�����、劉家麒����、孟兆禎、孫筱祥���、王秉洛���、楊雪芝、張樹林���、周干峙等�����。德高望重的前輩們的鼓勵(lì)和批評都充滿著真誠和關(guān)愛�����,因此始終都是我前行的路燈�����。
最后我還要感謝第一版熱心的讀者和關(guān)心我的各地的學(xué)生們和同行們��,我總能從他們的熱情中��,包括留在我網(wǎng)頁上的感人話語中�����,獲得無窮的力量和寬慰��。
2005年6月于海淀上地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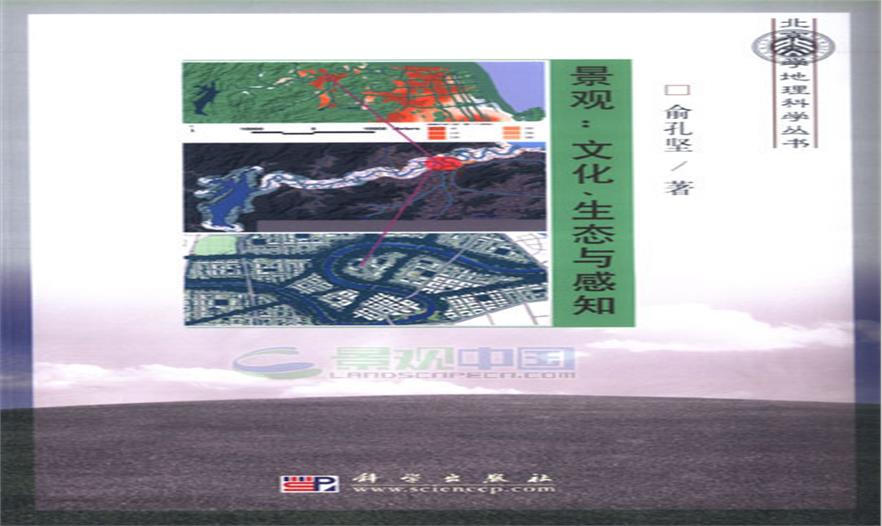
 京公海網(wǎng)安備 110108000058號
京公海網(wǎng)安備 110108000058號 北京朝陽區(qū)
北京朝陽區(qū)
